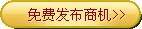记者从调查中发现,在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下,以河南为代表的粮食主产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确取得了不小成绩,普遍农民生活有较大改善。但由于城市就业收入更高,农业不能产生更多的货币收入,农村的能人精英大都用脚投票,到城里经商打工挣钱去了,剩下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农村的生产生活虽然有所改善,却难有更大发展空间。
“地还是值得照顾”
2013年,河南粮食总产达到1142.74亿斤,与全国同步实现了连续第十年增产。
“这与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有极大关系,也跟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著名“三农”学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对《南风窗》记者表示:“中国30多年来的社会稳定都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加上快速工业“靠种地赚不了钱,但也不辛苦。家里有人在外打打零工,再搞些养殖业,农村生活开支不大,这样的生活也可以。只要政府不耍赖,忽然把地收走了,地还是值得照顾的。”
把2亿多农民工吸收到了工商业,种粮人口少了,人均收益也就相对提高了。
中央还保持了对粮食的最低价收购政策,每年价格上涨一点,以适当抵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但由于农资价格涨幅过快,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平均每亩地年纯收入长期徘徊在300~500元。
记者到粮食主产区农村采访,发现中老年农民对2005年取消农业税政策尤其满意,因为他们都有过痛苦的纳税体验。2002年河南农民人均负担为66元,有的地方高达几百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3年。
取消农业税,粮食主产区农村的气氛是相对祥和的,当然,城乡结合部的征地,以及种粮补偿款被干部贪污、挪用的农村除外。河南周口商水县某村村支书,全家以及亲戚一二十人都吃低保,后被周口市纪委查处。有一个县套取国家粮农补贴近千万元,周口市纪委对此案查处后,引起省委领导重视,此后河南全省的粮农补贴都不再拨到县里,而是改用“一卡通”,直接打到老百姓卡上。
很多农民表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政策性负担了,有些负担是由市场因素或自身因素引起的,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恶性上涨几乎全部冲销了国家对农民补贴所带来的好处,令部分种粮农民仍觉负担沉重。
农村出现了两种新情况:一是新的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土地不能买卖,所以这种分化不可能产生在农业领域,而只能在工商业领域,这既与机会有关,也跟经商能力有关;二是新时代的“小富即安”。
陈丽平是开封县范村乡葛砦村一位农妇。家里分了6口半人的地,20亩,有12亩用来种花生。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种花生。种一亩花生能收五六百斤,毛收入1500~1600元。除掉种子、化肥、农药、灌溉等投入,净收入在500元左右。
陈丽平对《南风窗》记者笑道:“靠种地赚不了钱,但也不辛苦。忙这一阵,种完就没啥事了,浇浇地,上上肥,打两次除草剂就行了。收花生的时候,也是用花生收获机把地犁开,人跟在后面拾花生就行了。家里有人在外打打零工,再搞些养殖业,农村生活开支不大,这样的生活也可以。只要政府不耍赖,忽然把地收走了,地还是值得照顾的。”
但在隔黄河相望的新乡市农村,花生的种植面积逐年在减少。农民以前把一半地种花生,一半种玉米,现在有的全改成种玉米了,因为玉米好管理—农村缺劳力,种地的都是些五六十岁年纪,出去打工没人要的。
从调查中发现,因为生活和劳动压力都不太大,与城市里月收入较低工薪族相比,农民显然对现状的满意度更高。
一些农村也有新的发展。“我们那里的城镇化是从2009年开始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张继宗说。他的家乡在河南商丘市虞城稍岗乡白寺王楼村。“我们村的四周都是国道、省道等,邻近马路的地方全开发成了房子,农民们开超市、卖五金、开饭店、修摩托的都有,自发形成一条街市,挣到钱了的人都搬到那里去住,原来的村子成了空心村,有些村都推平了。”
开封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王载飞说:“现在我们还是侧重于硬件建设,有些离县城近的地方搞产业集聚区,变成‘新型农村社区’了,精神方面的重构和建设要滞后些,这也正常—总得先盖房子,先住到一块,然后再搞精神文明建设。”
粮食主产区的新问题
但在这种基本满意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与全国农村共同的一个问题是,青年农民工的出路。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外出务工大省,河南2000万农民工,有一半以上是在省外打工。现在农民工的主体是“80后”、“90后”一代,他们很少想再回到农村,而希望融入城镇。但,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吸纳人口极其有限。大城市倒是工业化充分发展,但想在当地真正生活下来,成本极高,低微的打工收入显然难以实现这种梦想。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农业劳动效率仍然较低,普通从事粮食种植的小农,其农业生产的收入仍然普遍低于城市工作收入。以前的问题是为农民减负,现在的问题是帮农民增收。尤其中西部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大县,工商业不发达,农民增收就更难。城郊结合部的农民,有房子可以出租,对于离城远的农民,外出打工仍是最直接、最便捷的收入方式。
农业税取消后,有些农民种地积极性反而不高了,有的不太好的地被撂荒。农业耕作对机械化、化学化的依赖程度普遍提高,但农民也懒得往土地里过多投入资金,因为“无论投资增加多少,产量都差不多,收益也不会有太大增长”。这种边际递减效应成为最现实的农民理性。
由于过量农药使用造成的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问题,在这里也时有发生。几年前,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袁楼村农民李建亭想在本村1000多亩花生地推广“无公害农业”,但村民们疑虑重重:“花生棵长不大咋办?结得少了咋办?将来拿出去卖给谁?你说你是‘无公害’,人家就相信了?”李建亭让儿子包了十来亩地搞试验,不打药,不上化肥,结果还真是长得赖:别人一亩地能收600~1000斤花生,他儿子一亩地只收100~200斤,想卖高价也卖不出去,因为人们不相信那真是“绿色花生”。
袁楼村的老人们说,过去治虫,是早上趁着有露水,把草木灰洒到花生地,现在是往地里打杀虫剂。“现在种这庄稼,种着种着,咱自己就把自己害了……”今年60岁的李建亭叹息。
难走的集体合作之路
河南曾涌现过很多“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典型,如漯河南街村、新乡七里营刘庄、濮阳市西辛庄等,它们都曾靠发展集体经济,迅速积累集体资产,引领村民富裕起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
但集体经济到底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活,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集体经济要想搞得好,首先需要一个“德才兼备”的带头人。所谓“德”,指其不谋私利,一心一意为集体利益着想;所谓“才”,是他有高超的市场运作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假如没有这两个条件,集体经济必死无疑。
问题是这种人如何产生?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有市场运作能力的人大都自己谋发展去了,完全不为自己,专为集体经济谋发展的人毕竟是少数。
其次,集体经济的领导班子成员,还必须都要有集体主义精神,不然他们迟早也会散伙。
曹锦清认为,从理论上讲,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难以兼容,因此,虽然集体经济以星星点点的状态存在还是可能的,但总体推进很难。
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组织的职能从行政领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进程并不顺利。一些村的两委成员逐渐兼职化,或在外办企业,承包公路修建、乡村桥井建设等工程。
近年来,像温铁军、何慧丽等一批热血知识分子,去农村寻找农民的合作化之路,力求改变农民分散、软弱的状态。但黄河岸边的农民们经济合作欠缺,合作意识、合作文化更欠缺。此外,希望合作的农民,首先会面临合作成本由谁来支付的问题,因此很难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力量。
某些金融专家期望“将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探索建立产权明晰的农民自己的股份合作金融组织,将资金资本化”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民间高利贷倒是在一些农村盛行起来。
也有的合作社处于变相和变异的境地。在河南某县,现有农民经济合作社300多家,大部分是在《合作社法》出台后成立的,因为合作社可以享受免税等多项优惠政策,这些名义上的“合作社”实际就是公司,社员其实是公司职工。它们的办公环境很漂亮,规章健全,有专业会计,需要什么报表都能做出来,很受政府欢迎,实际上却不会给农民分红,只是填个表而已。
招商引资是与非
在压力型体制、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得不以工业化为重,以招商引资为重。
河南一些传统农业大县,一般经济都较落后,招商引资是最直接促进发展、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方法。这里的县乡经济想发展起来,没有招商引资不可能;不招商引资,有的县乡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没有。因此,地方政府是发展地方工业化的招商引资的主体力量,而对于农民合作、生态农业和食品安全、恢复和重建已遭体系性破坏的农村环境等关键性问题或漠视,或应付。
而在工业增长乏力且收益缓慢的情况下,因为农地非农化产生极大的级差地租,土地成为各方争夺的核心资产,土地纠纷也成为农村众多矛盾的核心。一些地方的“并村运动”本质是为了获取农民的土地。一些招商引资项目只圈地不建厂。
“对于招商引资的主流要肯定。”开封市副市长王载飞说,“招商引资就是开放,一个地方要开放,要崛起,国家也是鼓励的。但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竞相压低门槛,提很多优惠条件,造成农村污染问题等等,这也不能完全怪基层……这些问题中央层面都意识到了,我们也意识到了,正在采取措施扭转。”
在“城乡建设用地统一市场”的中央新政策激发下,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河南省也开始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巨大空间大力想象乃至行动。据媒体报道:河南省有关官员估算,按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实现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通过对农村宅基地的复耕,可腾出超过500万亩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站在这种估算背后的,显然是大量的失地农民。
2013年12月25日,河南省委通过的《关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称:“一些地方在新型农村社区探索实践中偏离分类指导、科学规划、群众自愿、就业为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出现新村搬不进、旧村拆迁复垦难、财政债务负担重、运转难持续等问题。”
“三农”问题学者何慧丽颇感慨地表示:“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种商资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由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环境的成本破坏性之大,须高度警惕。这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